撰文:朱順慈(1993年畢業)
(本文輯錄自《鏗鏘一千1978-2003》 特刊,由朱順慈於2003年編輯成書,原文為朱撰寫蕭景路的人物專訪,標題為編者加上。)
「作文寫『我的志願』時,我會寫記者。」蕭景路說。
「我小學時已很喜歡看電影,那時我愛收集明星雜誌,又會到當時的油麻地戲院看戲。升上中學後,或者因為學校有少少「左派」成份,學生很積極參與學校和社會工作,我和同學常常結伴到普慶戲院看電影,由那時候開始,自己便相信人一定要服務社會。作文寫『我的志願』時,我會寫記者,覺得這是最理想的。」理想和現實之間,有時會鬧意見。立志成為記者的蕭景路預科成績不太好,幾乎跨不進大學門檻,後來獲中大英文系取錄,讀了兩年,一番周折才如願轉到新聞系。

『從九龍城坐車到鰂魚涌,居然沒有故事?』當時蕭在《南華早報》實習時的新聞編輯Kevin Sinclair總會質問她。
「暑假,我在《南華早報》實習,當時Kevin Sinclair 是新聞編輯,我跟了他兩個月,最需要學的都在那時學了。最初幾個星期覺得工作沒有甚麼刺激,直到一個星期天,那天所有突發記者都放假,發生了一宗巴士車禍,Sinclair便叫我到伊利沙伯醫院看看有甚麼故事。到了醫院,傷者都急救去了,要問資料卻誰都不理我,很凄涼。正發愁找不到故事,遇上巴士稽查,他可能見我可憐,便帶我去見那個出事的巴士司機,我興奮到不得了,訪問完立即打電話給Sinclair,他卻輕描淡寫,一句『有甚麼大不了(No Big Deal)!』便叫我返公司。雖然他沒有開口讚我,但卻讓我的名字出現在報導上(By-line),這是我第一個 bylined story。」
「Sinclair 第一次認真讚我,在我寫了第一個詳盡的人物特寫之後,主角是三藩市華裔女議員,在特寫中我說『三藩市未來市長訪香港』。Sinclair說故事寫得很好,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舞。」
「那時天天上班,他總會問我有甚麼故事?我總是說不上。他嘀咕: 『從九龍城坐車到鰂魚涌,居然沒有故事?』這幾乎成了他的『金句』,就是這『金句』提醒我觀察最重要,身邊故事其實多得很,問題是你有沒有留心罷了。」
蕭景路中大畢業後做過兩份工,其一是麗的電視英文宣傳主任。後來,拿了獎學金到夏威夷唸碩士。那年頭,教育電視方興未艾,蕭關心教育和媒介,於是專門研究。回港後,她一心想從事教育電視工作,寫了兩封求職信: 一份是天主教區視聽中心,一份是香港電台教育電視。前者沒覆,後者又說沒有空缺,結果轉了去公共事務組見工。《鏗鏘集》第一任監製倫紹銘正在籌備開播,節目需要助導,於是蕭景路77年底加入團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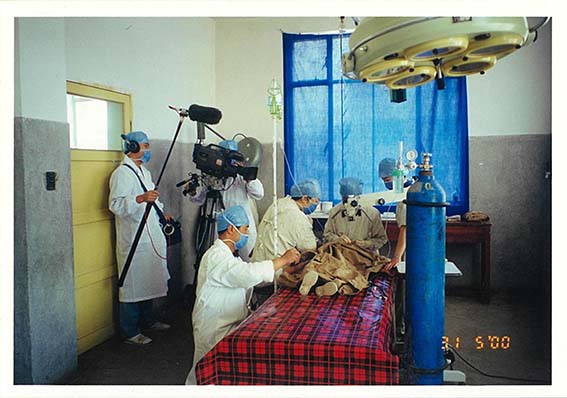
「現在想起做助導的日子,真是不識死。」
「我記得拍過一集講滑板的《一板風行》(1978) ,要拍一個汽車撞倒滑板少年的鏡頭(註: 當時《鏗鏘集》仍然是半真半戲的電視製作),我便駕了爸爸的老爺車來,還親自開車,真夠膽!現在有同事這樣做,我想我會反對吧。」
「我們都說拍紀錄片,但紀錄片是甚麼,其實不甚了了。」蕭景路回想早期的《鏗鏘集》如是說。
「初期的《鏗鏘集》題材廣泛,注重資料性,『場內場外』(1979),講馬場種種,現在回想其實沒有甚麼中心思想,但當時觀眾受落,覺得資料豐富。至於表達手法,節目早期用大量旁白,而且很多Wallpaper(牆紙),主要為配合旁白的畫面,少用被訪者的話,也很少由個案親身訴說自己的故事。 」
「拍『城寨』(1979, 蔡繼光導演),我們找來一個演員,由他帶領觀眾認識城寨。當時我不同意這個手法,但又說不清楚問題所在。因為真實性問題,我們討論過是否找城寨居民出鏡,但又怕不連貫。⋯⋯為什麼紀錄片又紀錄又演戲?之後,我越來越少用這手法,以至後期完全不用,採用純紀實手法,這轉變在其他導演作品也看到。對於真實的堅持,日子久了,大家越執著,有時因為拍攝跟不上而失了必要的畫面捕捉,導演會為要否著當事人做 一次而躊躇。」
「我拍『廟街行』(1982, 獲亞太廣播聯盟電視大獎)在廟街成功訪問了一個妓女感到開心,跟攝影隊吃飯時,攝影師卻懷疑妓女的話來,質疑她的話只不過是迎合傳媒。我還記得當下那感覺,所謂真假,並不是那麼容易看穿。眼前的事是真是假?如果是人物故事,當事人是否在說真話,很大程度取決於導演的掌握,但當事情涉及社會議題,導演便需要從不同角度去檢視,呈現不同立場,最後觀眾是否相信個別立場和觀點,應該留給觀眾而非導演去決定。」
1985年蕭景路正式出任《鏗鏘集》監製,負責為節目把關,對真假、公正、客觀持平等等,有更深等體會。

以偏蓋全,還是見微知著?
「我85年開始做監製以來,遇上不少挑戰。當年我們拍了兩集『私校』(1985),同事拍到一些私校內部的情況,顯示了私校的質素問題,我們又訪問到相關人士,但節目出街後,某些教育團體和教育署都有話說,節目無形中成了磨心,有人批評我們『以偏蓋全』,事件後來還鬧上電視新聞。」
「怎麼辦呢?我們收到指示要繼續搜集資料,回應『以偏蓋全』的批評。結果一組人跑遍全港私校拍照,找來更多資料,最後我們開了個攝影展,召開記者會,公佈資料。那時我大住肚子,壓力很大,但為了澄清批評,也得支撐。」
「大抵由那時開始,節目越來越尖銳,也越來越多人用『以偏蓋全』來批評我們。老實說, 一個電視節目,只有廿二分鐘,沒有可能把每一個細節都說清楚,社會事件這麼複雜,能夠處理的面向著實有限,所以我們要好清楚表達給觀眾知道這個限制。很明顯,製作人亦很難做到完全沒有立場(註: 後來,她也說過拍紀錄片沒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場,『各打五十大板』其實很懶,也不好看。),我們了解自己的局限,但無論如何,在製作過程中,我們提醒自己傳媒的責任,盡力符合公正,平衡和客觀的原則。雖然最終還是不能絕對全面,但終究也不是單純的『以偏蓋全』。⋯⋯過程中,不但製作人要成長,觀眾也要一起成長。」
電視製作,團隊至上。
「有一段日子,找誰旁述是導演視乎題材,各施各法。後來定了用劉家傑,很多觀眾真的以為稿是劉生寫的。事實上一稿要過劉家傑的關也不容易,他真的會給你推敲用詞的。劉生是性情中人,他做人很有原則,他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。他會對節目和同事提很尖銳的意見,他的意見非常重要。」

「我做導演時,對助導要求很高,但做監製久了,我變得包容了,更關心如何發掘每個同事的潛能。做一個領導者,要有胸襟接納別人,你不可能要求每個下屬都跟你一條心,在《鏗鏘集》,我更注重培養同事,而不是一不合適便把人踢走。」
「我很感謝這些年來《鏗鏘集》的同事,他們已成為我生活一部份,到要分別時,我一定會不捨得,一定會失落。老實講,對年資較輕的同事,我覺得他們更像是學生,我很想將自己所獲得的都教給他們。」
「廿多年過去,節目仍然很有動力,我從每一集每一個導演身上學了很多新事物,每次都有新的驚喜,一個好導演應該是一個說故事的能手。《鏗鏘集》最與別不同的是,它每星期都給你新的、不同故事。」
(後記: 蕭景路03年提早退休,離開港台,當時是執掌整個教育電視的主管。蕭退而不休,續在浸大電影系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紀錄片,期間也到中小學辦傳媒教育。她形容那一段日子,常常拖著一個小行李箱穿梭於學校之間,很忙碌也很充實。)



 Follow
Follow